522 曦夢逐影:夜囚之章
情報 序章 第1日 第2日 第3日 第4日 第5日 末章 結束 / 最新
[1] [2]
[備忘 自言備忘 匿名備忘/履歷] / 發言欄
代理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代理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代理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代理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代理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代理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代理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代理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禮拜堂內穆肅而莊嚴的禮拜堂裹著七彩光華,羅莎披著白紗在臺上踏著詭異的舞步,哼唱基督的讚美詩,玻璃球的眼珠無神卻映著虹光,灰色長髮隨著舞步撩動,她看似沒有打算理會剛從棺木裡出來的你們,畢竟她的入殮手法從來沒失誤過。 待所有人都起身,她才停下腳步面向眾人,右手一揮前方的棺木瞬間都隱沒於曦光中,禮拜堂空間頓時變的寬敞許多。 「很好,各位。」羅莎正在說話,但聲音卻是你們熟悉的低沉男聲。 是弗里克,他正用著洋娃娃羅莎的嘴和你們對話。 「既然戲已落幕,對你們的測試也有了滿意的結果,來吧!抉擇吧。」 羅莎張開雙手,接著一位僕從提著燈籠漫步走到羅莎後方排成一列。 「獲得你們所謂的自由,或是跟隨我?」 燈籠頓時發出強烈的白光,像是在促使你們抉擇。 (#0) 2024/04/26 (五) 21:32:45 |
(n1) 2024/04/26 (五) 21:35:43 |
禮拜堂內選擇跟隨弗里克的你們,依然留在禮拜堂內。 「我忠誠的門徒啊,我將永恆與祝福賜於你們。」 說完,羅莎閉上眼,弗里克的聲音唱起古老的樂曲,頌讚基督的詩歌,此時禮拜堂內的七彩晨曦像是有意識般的攪動著,隨後你們被無形的力量拉起浮在半空,無法掙扎。 隨著詩歌唱到激昂之處,七彩晨曦開始大量從你們的眼、耳、口、鼻進入你們的身體,煉化你們的靈魂,期間會感受到撕裂或灼熱感,可能是極大的痛苦,但你們沒辦法叫出聲來,沒辦法阻止晨曦的賜福。 曲畢,你們緩緩降至地面,禮拜堂和初始一樣莊嚴穆肅,但你知道自己體內有種不一樣的能量在流動。 「如此,你們靈魂昇華了。」 儀式結束,羅沙倒坐在地上,弗里克貌似也已經離開了。 (#1) 2024/04/26 (五) 21:36:59 |
(n2) 2024/04/26 (五) 21:38:33 |
火焰內部的獵手方你們的身周燃起烈焰,像是一道屏風,隔開你們、禮拜堂內的人和後方的樹林。 若有人真的要來,只會像撞到隱形的牆,看不見也無法聽聞裡頭的情況。 屏障裡的貓頭鷹行跡詭異,似乎要甩下身上發亮的金屬物,而不斷拍打翅膀,穿梭在火焰中繞行,卻一點損傷都沒有。 除此之外,火牆內一點異狀都沒有。 卡洛琳點點頭,示意你們把手臂橫置在胸前,貓頭鷹們終於擺脫束縛似的,一一飛到你們手上站好。 而他們頸子上戴著的,是鑲著寶石,繫在長金屬鍊上的發光項鍊。 至少,落在西奧多手裡的是完整的項鍊。金色長鍊的末端綴著拇指前端大小,如滿月般溫潤的半透明球體,內裏還有一株鮮綠嫩芽,如果選擇踏入暮影,可以直接將核心鑲嵌在球體內。 卡爾的吊墜上,僅有空的銅製台座,似乎是羽毛的形狀,而一隻激動的雪鴞像網球一樣撞破禮拜窗,往藥師的臉衝去。 剩下一隻黃毛小鵰鴞,它可能還是個菜雞,因此隨著破窗的前輩而去,把均分成冰藍和翠綠的橄欖型寶石砸到米羅頭上,叼著空底座去向諾拉顯擺。 (#2) 2024/04/26 (五) 21:45:28 |
(n6) 2024/04/26 (五) 21:50:44 |
(n8) 2024/04/26 (五) 21:52:59 |
 | 歌者 路易絲靈魂昇華的痛苦讓路易絲進入短暫的昏迷,任由晨曦在自己浮空且無意識的身體內亂竄,而腦海中最黑暗的角落,被身藏已久的記憶也因黎明而甦醒。
------ 大約是十八世紀,因為奧地利王位繼承權而引發的外敵入侵戰爭開打近一年,他,路易斯以奧地利士兵的身分踏進了戰場,可是還沒等到自己立功,所屬的部隊就被法軍擊潰,幾近全滅,而自己連同生存下來的戰友們還來不及慶幸大難不死,就全被法軍抓去當戰俘。 活下來就好......活下來就好...... 一開始法軍勢如破竹,接連贏了好幾場大小型戰役,士氣高昂的法軍高層也沒有太為難戰俘們,除了被關在壅擠的小房間內,吃穿拉撒都不成問題,甚至還有機會在他們慶祝的晚宴上被叫出來表演,歌唱、跳舞,各種才藝,只要表演精彩都可以獲得暫時的優待,儘管成為玩物沒有尊嚴,但戰俘們還是搶著表現自己,讓俘虜生活更輕鬆一點。 不要尊嚴也沒關係.....能活著就好...... 天佑奧地利,戰局開始反轉,法軍戰役上節節敗退,連補給線也時常被奧軍封鎖破壞,食物短缺導致軍隊士氣低迷,高層為了提振士氣更常叫俘虜們出來表演,食物缺乏讓戰俘們更加渴望為敵軍獻藝,以此獲得更多的食物填飽自己,另一方面為了減少食物消耗,法軍開始處理殺死沒有才藝的戰俘。 路易斯憑藉著上帝賜給自己的歌喉,成功得到了數次表演換食的機會,某一次一個同胞在和自己合唱時因為唱錯調,當場被用長劍刺穿喉嚨,另一名同胞因為嚇到停止歌唱,也直接被長劍斬首,而自己全身沾滿同胞溫熱的鮮血,眼前更有驚恐的同胞頭顱盯著自己,路易斯還是面無表情的繼續唱完讚美詩,最後贏得滿堂掌聲與歡呼。 我必需要唱......我要活下去...... 法軍處境越來越艱難,士官兵們已經開始不滿足於歌唱跳舞,他們需要女人發洩,或是可以當成女人的戰俘們,俘虜們依然表演著才藝,只是犯錯不是死,而是會被帶去隱密處內滿足法軍的慾望。 之後俘虜開始出現自殺行為,已經不太壅擠的小房間漸漸變空曠,很快就只剩幾人,最後俘虜們也不用再回到小房間,就是一直待在士官兵房內供人享樂,甚至不用帶去隱密處,是直接在眾人面前被當母狗發洩,不管是後庭、手、嘴,都沒日沒夜的被侵犯著。 不知道過了多久,所有新、舊俘虜都因為不配合士官兵發洩而被毆打致死,只剩路依斯精神錯亂的還堅持著。 再來......我要活下去.....繼續...... 最後,奧地利贏得了戰爭,路易斯躺在空蕩蕩的法軍軍營內奄奄一息,彌留之際最後看到一雙腳走到自己身邊,蹲下來輕輕地說著話。 「你想要活下去嗎?」 ------ 「我想活下去!」 路依絲大喊,猛然睜開眼,發現自己站在禮拜堂的地面上,她的臉龐已被不斷流下的眼淚浸濕,身體還在劇烈發抖,此刻她只感覺到體內卻有一股神奇的能量在運行,而過往不堪像是又躲了起來,她怎樣也想不起來剛才腦內閃過的百年記憶。 |
 | 守墓人 奧爾>>#0>>n1
奧爾幾乎是要不認得弗里克的聲音,那當然不是他的聲音,他指的是那人說話的語氣、那人的形貌、那人曾對他做的一切……彷彿在靈魂脫離身體後都不再鮮明。視野開始變得模糊,他似乎是笑著拒絕了女聲的提案,接過了戒指,不記得這抹嘴角的弧度是源自於身體裡的哪個記憶。 離開莊園,他好像很久沒有走在陽光灑落的哈修塔特鎮上,眼前的明媚風光與褪色的回憶交錯湧現,他試圖尋找他曾經的居所,在鎮中晃了幾圈,便轉而將步履移往墓園。 一一細數石碑上的名字,奧爾找到了曾經屬於自己的姓氏,他的父母、兄長們皆臥在冰冷的墓土之下,他還找到了一些過去的朋友,以及曾掛在心上的戀慕之人。 他無法想像他不曾參與過的他們的老年,甚或連他們與自己分別時的樣貌都曖昧不清,他回想起他努力釐清的那些頭緒,那些理由和呼喚,不過是源自於自身的孤獨,在他漫長且空洞的生命裡響徹的回音。 守墓人無法親手埋藏自己的身體,至少還能為自己選擇合適的終點。 他端詳著那嵌於戒指上晦暗核心,旋即握入掌心收緊,將自己的靈魂連同其桎梏一同粉碎,大臂一振,把所有回憶全數擲入哈修塔特湖裡。 他的身軀坐倒在地上,倚著故人的墓碑,回到時間停止流動的那天。 天上的星星不再閃耀,靈魂在黎明的光中逐漸消融。 奧爾闔上了雙眼,如同一百年前開始不再擁有心跳。 |
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 歌者 路易絲>>3
從巨大的疼痛中緩了過來,並正在消化信使那段聽起來沒有幫助地講解,路克安靜的出現在身邊讓路易斯下意識的彈了一下。 「啊!是路克先生,我失態了。」捂著自己的胸口,稍帶歉意的微笑。 路易絲看著路克遞來的絲綢,伸手撫上絲滑的料子,表情驚喜的看著對方,心裡想著這布料如果上了自己身一定會很美。 「果然是上好的料子。」 她轉頭看著手裡路克的卡片,眼神瞇成線後視線再轉向眼前男子。 「我會找時間上門拜訪的,我可是很期待路克先生為我設計的作品呢。」 路易絲還是不太明白為路克的選擇,渴望真的可以讓一個人放棄強大的庇護和安穩的生活嗎? 我的渴望……歌唱和性? 更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執著於這兩件事,可能和想不起來的過去有關吧。 「路克先生,如果你來到維也納,在紙醉金迷之處你一定可以找到我。」 路易斯的臉迅速貼向路克的耳,她用芬芳的喘息在他耳邊輕聲說著。 「我等你。」 說完,路易絲嘴角勾起狡猾的笑容。 |
 | 顛茄 藥師>>#0 >>#1
男人似是凝望著說話的玩偶,眼神卻像深深看進發話者靈魂那般令人顫慄,但他並未轉身離去、而是冷冷地向前站了半步,彷彿在昭示他對於繁複流程的不滿。 七色的歌聲將人拉升,藥師並未掙扎、也未曾闔上雙眼,好似那些灼燒與撕裂都與他無關、甚至感受不到,他只是靜靜地看著身邊的人或昏迷、或面目猙獰,然後一團火光自他體內迸發,耀眼的藍將他的身軀吞噬、包裹晨曦,最終將那進入靈魂的七彩詩歌煉入男人的身軀之內。 純粹的藍焰在那一剎那間炸開,男性、女性、老者、幼童的嚎哭彷彿在耳邊纏繞,藥師的身軀逐漸在那七彩斑斕的純藍中消失,靈魂燒灼的味道在莊嚴的賜福中溢出,那似乎來自更遙遠的過去。 作為焰心的男人闔上雙眼。 他依稀聽見那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曾經為升天的聖人而朗誦的禱詞、古希臘詩人口中的情歌、在烏爾帝國中傳唱的人聲,然後是爭吵、謾罵、兵戎相見,吵雜的聲音從男人的靈魂深處鑽出,掩蓋了那些祈禱、讚頌、少女純粹的歌聲。 ——我詛咒你。 然後那一連串的苦難之聲開始被冰凍,自體內燃燒的火焰除去了炙熱,被更加極端的寒冷所收攏、匯聚,最終停滯於男人的手心,隨著焚燒靈魂的味道與藍焰一併消失,那個被喚作藥師的男人將手心中的火焰吞入口中。 詩歌停了,男人平穩地落於地面,沒有痛苦、沒有哭嚎、也沒有幸福,只有平靜的風在身邊吹起,他身周的空氣變得更為冰冷了些。 男人睜開雙眼。 |
 | 顛茄 藥師>>5 >>@0
藥師冷冷地看向那個惡狠狠的發話人,然而那雙紫藍色的瞳中似有甚麼變得不同了,他在對方說完話後靜靜地走到羅莎身旁駐足,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少女。 「當心您不合時宜的慈悲,我們往往無法得知自己是否放走了猶大,或將大門敞開給特洛伊的木馬,莫要妄想做聖父子。」 他略顯冷漠地說道,好似是在和那名少女說話,但卻更是在那背後的那人言語。 「我不信甚麼耶和華,您也只會是我的尊主,而不能是我的蓋亞、弗里克。」 只見男人從他腰上的藥草袋中取出一朵金盞菊,蹲下身去放到了羅莎的手中,然而那一朵鮮艷的花從藥師手中脫離後便迅速枯萎、凋零,最終那朵變得枯黑的花在少女手中被風吹散。 「我對這一次的集會準備與封賞都感到不滿,希望下一次能看到些不同,告辭。」 語畢,男人站起身來往門口走去。 一步、兩步,隨著那一縷從腳下延燒開來的藍色火光,藥師整個人被那冰冷的火焰包裹,最終消失在禮拜堂內。 |
 | 顛茄 藥師>>6 >>n7 >>0:21
那一縷火光出現在樹林中,從中映出了男人的身姿後又熄滅,他悄悄地摘走了那朵鱗柄白鵝膏,隨後順著血腥味來到了北側的湖邊,看見了那個渾身是血的女孩。 而他只是緩緩地走到她身邊蹲了下來,將指節湊近對方的鼻尖。 「……還能有一口氣啊。」 然後藍色的火焰從男人的手中併發,將女孩身上沾染而未乾的血液一併燒盡,接著他從腰間的皮袋子中取出一瓶藥水,捏著瑪娜的下顎強硬地灌入她的喉中,又動作流利地為人清創、上藥、包紮,彷彿他是在幫人處理膝蓋的擦傷、而不是救一個將死之人。 「要是能好好的熬過去,妳也能算是一枚好胚子了,既然妳的家和公爵府都看不上妳這枚原礦、那就來做我的學子吧。」 只見一個響指,男人的凍焰便將女孩和她長著翅膀的朋友們一併送離,或許等女孩再次醒來、她會躺在一張柔軟而潔白的床上。 只是他還不能離開,他還在等著人。 |
 | 記者 卡爾>>@1>>#2>>@2
刻意做舊or的銅製的吊墜框被工匠打造成飛羽的樣子,金屬的反光映著不清楚的面容,卡爾持著長鏈,望著墜飾裡面搖搖晃晃的『自己』。 不過是虛影罷了。 「夜晚並不溫柔,只是將殘忍平分給了身處噩夢中的孩子而已。」 卡爾面對白袍女子的笑容淡淡地開口,而後轉頭看向雪鴞飛去的方向,倒也沒有要繼續辯駁的意思。 「而自由也從來都不是能夠由自己決定的東西,請弗里克先生好自為之吧。」 這仗無論成功或失敗,他都不打算讓『卡爾』活下去了。他握緊了那個空空如也的吊飾框,即使是輕柔若羽的造型,金屬的邊角依然扎得人手疼,才剛被修復好的軀體,掌心的物件刺入肉中,鮮血緩緩地流了出來。 他自燒盡的禮拜堂走出,要去赴一個約。 |
 | 顛茄 藥師>>7 >>#2 >>@2
一隻雪鴞遠遠地飛來,男人伸手接住讓牠平穩落下。 然而單薄的布料承受不住激動的鳥爪,銳利的指尖勾破了藥師手臂的皮肉,但他似乎不怎麼在意,令人懷疑他是否被奪去了知覺。 看到雪鴞帶來的寶石,男人立刻就知道那是甚麼樣的一個東西,也明白蘊藏在這封無字信函裡的含意,於是他取下貓頭鷹脖子上掛著地寶石,隨後從腰間的皮袋子裡找出一些奧勒岡葉,像獎勵乖巧的鳥兒一般送到雪鴞的嘴邊。 然而他沒有對那顆寶石做出更多,只是在仔細端詳後謹慎地握在手心裡,並闔上眼隔著手指輕輕親吻,彷彿他正在向戀慕之人的靈魂低語無聲的愛意。 他睜開雙眼。 「卡洛琳……嗎……」 藥師輕輕撫摸那隻乖巧的雪鴞,並任著小鳥輕輕啃咬自己的指節,於是他將那隻貓頭鷹放到自己的肩上。 「那麼你也和我一起回去吧。」 |
 | 記者 卡爾>>9
卡爾緩步往北,沿著被清晨陽光照得波光粼粼的湖邊,慢慢地前行。 他並不討厭陽光,甚至有點喜歡那份暖和,即使相對應的不適體現到了身上,也不會抹消掉這種喜歡。 掌心的血染紅了整個金屬框,從指縫滴滴答答斷斷續續地落到地面。 慢慢地,隨著那不快不慢的步伐,建築越來越少,道路從磚變成了泥土,卡爾看也沒看便進入了樹林。 他得去找到那個人。 終於他從土壤與樹皮的氣味中分辨出了那縷摻雜了血腥味的薄荷香,卡爾撥開樹叢,先是望向男人肩膀上的雪鴞,然後看向他手裡晶瑩的寶石,最後才對上男人的視線。 「你好呀,還記得我嗎?我訪問過你和你的苗圃。」 卡爾似笑非笑地重複了一遍他們於此百年重逢的第一個句子,像是要假裝整個夜晚的鬧劇並不存在。但是已經發生過的故事,又豈是能說改就改的? 「現在,你真正地握著我的生命了。」 卡爾的聲音輕緩如羽。 「怎麼樣,反悔了麼?你隨時都可以殺了我噢。」 |
 | 顛茄 藥師>>10
男人聞聲轉身。 「……我認得你,仍在做鵜鶘的孩子嗎?」 藥師愣了一瞬,還是刻意用第一次被詢問時的話回應對方的提問,卻無法馬上理解對方的用意,於是又馬上開口補充道: 「我不記得你我有過相認暗語的約定,但若你想、我可以配合。」 陽光和微風暖洋洋的撒在兩人之間,一夜過去、兩人之間或許都難免變得有些不同,又有誰是能一路走來皆如最初的模樣,然而他仍然如最初那樣固執而認真,甚至那樣的淡漠在這之中都有些滑稽了起來,彷彿他從始而終都是那個一本正經的男人。 彷彿在昭示著他從未變過、兩人的關係也不可能由他開始改變,彷彿在表達時間寫下的故事、只能由作者來詮釋。 「關於這個問題,我應該已經給過你明確的回答了。」 語畢,那股隸屬於他的藍色火光自男人的掌心中竄起,他以自己的凍焰包裹、謹慎地保護那顆寶石,接著只見男人就在卡爾的面前抬手、仰頭,竟是那樣慎重地將其整顆吞入口中、嚥下,異物感讓他的眉間皺了一瞬,但馬上又重歸平靜。 「……你妄要見證這個人世,我卻看不見在你筆下有你自身的位置,因此我也誓要見證完你所有未完成的記事。」 男人堅定地看向卡爾,沒有笑容的表情讓他的話更像一種真誠的發誓。 「所以在你完成所有故事前,我會守護你的生命不受侵擾。」 |
 | 記者 卡爾>>11
這個人還真是單純過頭了啊。逗起來還有點有趣,怎麼會這樣呢?卡爾在微風中鬆開了握緊的拳頭,等待鑲嵌的銅色羽毛被鍊子吊著,在風中搖晃著,像是拴著腳鍊的金絲雀。 該是有些沉重的心情,硬是被那個稱為藥師的男人往上提起,變得輕盈。 歷史總會迎來一個節點,卡爾是要來這裡寫上一個句號的,譬如那些報紙上的文章最終都會中止在那個標點。 正想揶揄兩句,卡爾張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著藥師的一連串動作,沒來得及阻止,自己的生命便那樣順著食道落入了對方的胃袋。 「你做什麼……喂、等——」 卡爾回想起幾種用於人類噎到食物時會採用的急救方法,卻在扯住對方的領子時沉默了下來。 「我連選擇死亡的權利都被你吞食了,現在可好,我的全部都屬於你了……還講得像是要催我稿的樣子,我的總編都不會這樣對我說話。」 他用受傷的右手撫過藥師的臉,在那消瘦又蒼白的肌膚抹上自己的血液,惡狠狠地靠著男人的耳朵輕語。 然後在兩人鼻息交錯、幾乎要吻上去的時候將距離拉開。 卡爾認真地望著藥師的眼睛。 「——你知道我的本名不是卡爾。對吧?」 話鋒一轉,卻是完全無關的別的話題了。 他用了肯定句。 而藥師胸前則多了一個血跡斑斑的項鍊,墜飾看似未完成的銅製小臺座,在應該要有寶石鑲嵌的圓形下方是一片精雕細琢的羽毛。 |
 | 顛茄 藥師>>12
寶石落入食道、在火焰的指引下嵌入身體內、最終懸吊於男人的心側一同鼓動、與他的血肉化作一體,硬物隨著他的呼吸帶來鈍痛,但他只是面無表情地接受了守護靈魂的代價,使這副皮囊成為脆弱靈魂堅硬外殼。 他的肉身本就不屬於自己,因此他也並不在意那些疼痛。 男人、女人、老者、幼童,那些都曾是他肉體的主人,而他殘忍地將那些人的靈魂扯出、侵占軀殼,成為那殺戮無數的罪人,他的容貌已經變換過無數次,最終也只剩靈魂才真正屬於他自己。 但。 本就是人類的罪讓他誕生,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捕食、又何稱邪惡,為了活著而進行的掠奪、又有何可恨,人類冠給自己許多的罵名,卻又做著比自己更殘忍的事,他想不明白、也不再去想開。 於是他也恨著人類。 於是他的造物成為了他身邊的空氣,一個又一個誓要斬殺被喚作魔鬼的自己,一個又一個死在了路上,因為壽命、因為毒、因為人類。 於是他由仇恨而生,也終成為了仇恨的催化劑。 於是再沒有人看見隱於人類之後,不斷變換的臉孔。 於是他沒有名字。 他向面前嶄露一瞬驚惶的人投去了一個溫柔的笑。 「……呵呵、那可真是幸好我並非你的總編,你想拖一世紀的稿也沒什麼問題。」 藥師難得向人開了玩笑,任由對方扯住自己的衣領、任由對方將自己的臉添上一抹紅色、任由那人為自己戴上項圈,他或許是在長久的生命中第一次感到欣喜。 因為如此、他們會擁有彼此。 「嗯,我知道。」 你看見了我,我也看見了你。 所以我不願以那虛假的名字稱呼你。 |
 | 記者 卡爾>>13
卡爾聽見了回答,輕快地笑了笑,他一直記得夜裡的許諾(>>1:43),儘管他並不相信他人的約定,卻會是一個守約的人。 以真實的你,與真實的我。 樹間灑落的微光在地面上晃蕩,他很快地接受了靈魂被掌控的事實。——他甚至有點開心,但是他才不會說出口呢or。 「卡艾勒姆。」 「這是我的母親給予我的,最初的名字。是天空的意思噢。」 卡爾——卡艾勒姆望向樹葉間被剪裁得破碎的天空,想起了很小很小的時候,母親會牽著自己在清爽的夜裡在原野間散步。彼時他還不知道母親懷胎的艱辛,不知道應當守身修行的少女為了什麼被驅離森林裡的部落,不知道為什麼其他孩子都有爸爸,他卻只有媽媽。 混血吸血鬼幼兒的成長曲線和人類或純血種都不同,他們的身心幾乎不以人類的基準成長,或許更加快速,或許遲緩,更多的是不穩定的跳躍式成長,身體與心智年齡常常無法對等地成長,直到肉體成熟。 卡艾勒姆十歲的時候才擁有人類三歲的外觀or,母親似是絲毫不在意獨自地扶養著偶爾因為吸血衝動而發狂的孩子,手腕上滿是咬痕與刀子的劃痕。 「凱,你要學著去愛這個世界。」母親辨識著星象,呼吸著草和土壤的味道。她出身自森林,學習的知識和術法繞不開與自然的對話,即使離開了森林,也沒有忘記長老們的諄諄教誨。 「人們畏懼著我們,我們卻要和他們共存。無論是短生的人類,或是長生的種族,都僅僅只是芸芸眾生的一部分,在本質上沒有不同。」 卡艾勒姆不懂地望著母親。 「在你的時間裡,我的存在或許只會佔據千分之一的時間吧,或許更少,卻是無法抹滅的日子。」母親輕輕地覆在孩子頭上的手是那樣的溫柔,「所以請好好地去愛人,去習慣離別,去擁有新的相遇。像天空那樣,溫柔地擁抱著這個世界……毋論善惡。」 可是我無法習慣離別,母親。 卡艾勒姆在埋葬母親的時候跪在草草埋葬的土丘前無聲地哭泣。他們輾轉於各個村落,甚至跟著北方的游牧民族生活過一段時間,最後母子離群索居,不再流浪,只因為年邁的母親再也走不動了。 只有母親是卡艾勒姆的世界。 不會有任何人記得這個犯了戒律的女人,她是不該存在的汙點,只有卡艾勒姆會記得那名女人逐漸衰老的模樣,而自己只能永遠是人類二十歲的模樣。 雷同的故事或許很多,卻不會留下任何紀錄。只有自己肖似母親的綠色眼睛和臉部輪廓證明了她確實存在過。作為吸血鬼,即便能夠,他也從來沒有動過替換身體的念頭,只因為那是卡艾勒姆僅剩的,母親的遺物。 但是我現在可能可以理解『愛』了,迥異於對母親的孺慕,卻又有那麼點相似——在千年之後的現在。 「光靠我的紀錄是不夠的,我只有一雙眼與一雙手。而鵜鶘已經成了氣候,他們都是我的眼睛,我為此感到驕傲。」卡爾注視自己的雙手,卡艾勒姆距離自己已然太過遙遠了,他不再是那個懵懂的孩子,在時間的打磨中逐漸變得圓滑世故,依憑著對母親的思念,培育出了能夠跟上人類時代劇烈變化的『紀錄者』們。 「從今往後,我不再為世人書寫,我只寫我想寫的。」 而今他總算能夠將卡爾殺死了。 卡艾勒姆轉頭輕輕扯了扯自己替那名男人戴上的項鍊,笑得有些狡猾。 「比方說,『我們』。」 被吞噬的究竟是誰呢?或許並不只有他而已。 像是宿命一樣,他們終將血肉模糊地混雜在一起,再也不分你我,直到世界盡頭。 |
代理村長已將村莊更新日延長。
 | 顛茄 藥師>>14
「卡艾勒姆。」 男人以古老的語言慎重地將對方的名字覆誦了一次,像是得知了神的真名、或是得到了君主的至寶,必須要用這樣的方式將那份贈禮揉進自己的心中,在一片思緒裡佔有那個最神聖而不可侵的王座。 然後他才敢將略為低下的視線再次落於對方面上。 「……我記住了。」 沒有多餘的甜言蜜語、沒有冗長的誓約禱詞、沒有虛假的欺瞞謊言,他的回答無比簡單,卻比任何約定都更加有份量。 「如此,我想這份記敘不會有太多高潮迭起的橋段,但或許會比你歷來所有的著作都要長上不少。」 男人這麼說著,臉上帶著溫柔的薄笑,然後輕輕地將那隻扯了自己脖上吊墜的手執起,並像手握十字架般闔上眼對手中的掌心告解。 「只有你告知真名未免有些不公,但……我沒有名字。」 接著,他在那人的無名指根部留下一圈淡淡的咬痕。 「你願意為我賜名嗎?」 |
 | 發條 雀斯坦>>#0>>n1
經過體感漫長又不間斷的討論,雀斯坦一時間疲累,隨意找了個位置坐下。弗里克的嗓音從洋娃娃口中傳出,如此不協調的場面中他抬起眉,燈籠的白光映在那雙薄綠的如貓一般的眼裡,十分眩目。 雀斯坦並不急著抉擇,手裡擺弄著樣式早已不時興的懷錶,拇指撫過鏤刻著常春藤floweror的錶殼。鐘錶店初創之際磨練手藝的首作,至今仍細數著分秒,令他在時間的洪流中有所依歸。 如同起初壓尾的赴宴,最後他也是遲遲上前。 「東西還我吧。」他微彎下腰,伸出手,「合作案可以,但我不習慣被束著。」 他垂眼看自己被鑲嵌著的核心,妥善將戒指收好,同時從衣服內袋抽出一張名片,放在羅莎身旁。動作行雲流水、理所當然。 「替我問好。」雀斯坦沒有指名道姓,維持著一貫平穩,「後會有期。」 |
 | 穹羽 卡爾>>15
「如果覺得我的名字過於難念,你可以跟我的……母親一樣,將其略稱為凱。」 卡爾對於眼前的男人總是在這樣的事情上表達出慎重隱約察覺到了一些東西,講出此番話,只希望兩人能夠更加對等地相處,他希望對方不要把卡艾勒姆當成遙不可及的天空,更希望卡艾勒姆是能夠被捧在手心裡玻璃球裡面的天空造景。 他們對於『愛』的認知或許皆與人類定義的概念有極大差距,但那又何妨?價值觀的衝突一直是有趣的議題,卡爾並不討厭和對方探討這些,甚至有些期待。 經歷了幾百年的孤獨,能夠有人並行,已是莫大的幸事——儘管對方對於世界的變遷頗有些怨言,那也是他的可愛之處。 「要我替你取名啊……那可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確定就要這樣託付給我?」 卡爾對於『藥師』的身分確實有些猜測,知曉對方自誕生以來便沒有姓名更是佐證了某些想法,但是他不急著討要真相,未來總有機會能從本人的嘴裡獲知全貌。 卡艾勒姆在草創鵜鶘的時候,從千千萬萬個常見又平凡親人的名字中,挑中了起源於德語的『卡爾』。 其意義為,自由。 ——儘管自由從來不是自己能夠抉擇的東西。 「既然卡艾勒姆復活了,那麼我把理當死去的卡爾託付給你,如何?」 卡艾勒姆以掌心撫上未曾獲得過名字的男人的手,半開玩笑半是認真地問道。 |
 | 歌者 路易絲湖風捎來的樹葉飛舞,拂過靠在馬車窗邊白皙的臉,像是小鎮正試圖挽留離開的路易絲,她回過頭看著湖面波光粼粼,與湛藍天空相映相依,與昨天到來時一模一樣,彷彿昨日鎮中的殺戮和猜忌只是夢一場。
然而體內流淌的力量和行李箱中的樂譜,卻訴說著昨日一切的真實不虛。 「門徒啊......」 路易絲閉上眼深呼吸,然後猛然睜眼大喊。 「X%&^$的弗里克!」 馬車伴著優美的汙穢詞語緩緩進入樹林中,往維也納駛去。 |
 | 顛茄 藥師>>17
聽完對方的提議,男人沉默地思考了一刻,隨後才緩緩開口:「……不,懷著祝福的名字是一種饋贈,只因口語的複雜而逃避是不敬的,不過若你願意,我會選擇那麼呼喚你。」 男人一面說著,一隻手輕輕觸碰卡艾勒姆的臉頰,淡淡的笑中透出幾分略帶擔憂的希冀。 「同時希望你了解,我並非要奪去令堂的愛語,那份愛稱既是你願意回憶的過去,就不應只是過去的念想,更要成為你的現在與未來。」 說完,男人肩上的雪鴞充滿靈性地拍了幾下翅膀,令他的頭髮也隨之飛揚,而髮絲下的一雙眼是那樣的堅定。 「好,那麼從今往後,我便是、也只會是你的卡爾。」 他笑著給予了自己的答覆,並溫柔地牽起對方的手。 如此,從今往後再也沒有被喚作藥師的男人和被喚作卡爾的記者。 有的只剩名為卡爾的男人與名為卡艾勒姆的男人。 「同我一起走吧,凱。」 想必那將會是一本漫長的私奔。 |
 | 穹羽 卡爾▲決定>>19
「沒情趣的笨蛋!」我會允許你那樣喚我,是因為我愛你啊。 卡艾勒姆對這個人的價值觀實在沒輒,又扯了扯自己替他戴上的項鍊,像是在拉扯一隻頑固的大型犬。 嗯,手感還不錯。 「洗鍊的語言能夠讓文章更好讀懂,而名字的縮寫不過是一種方便,」他停頓了須臾,「雖然說,確實很久沒有人那樣呼喚我了。」 「我們『現在』交談的每一秒,都是上一秒的『未來』。但你知道我不會滿足於此,我依舊樂於見識人類的能耐。」 卡艾勒姆的綠色的眼睛像是漂亮的玻璃珠,映照著天空。 「嗯,走吧,『卡爾』。」 對著這個人喊自己用了幾百年的名字讓卡艾勒姆莫名地有些彆扭,有些想哭,又有些想笑。 未來會如何呢? 日趨發達的工業技術想必會造成世界的劇變,比方說電能的普及,在維也納的市區夜裡已經聞不見煤油燈的味道。 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著作中的名言於此時依然通用。誰也不知道會不會再度上演類似法國大革命的事件,人類血液中的貪慾與好戰刻進了血脈,或許哪天又會爆發新的衝突。 那些都與我無關。卡艾勒姆想,他要做的依舊只是『見證』。 或許現在還多了『保護』,也不知道卡爾的居所在哪呢?如果哪天戰爭爆發,屬於卡爾的財產還是派得上用場的吧。 小記者的失蹤案想必不會獲得社會太大的關注,對應黎明組織的叛逃方案也早有規劃,鵜鶘就算沒有他的監督也能自由運轉,計算起來應是萬無一失。 就是有些對不起貝克小姐了(>>0:16)。 卡艾勒姆在一瞬間內規畫好了接下來該做的事情,心情是前所未有的開闊。 他握緊了對方的手,不想要再分開了。 這篇文章的句點終於被劃下,但是新的篇章即將要開始。 或許會有些無趣,或許不會被世人所接納,但是那將會是僅屬於這兩人的故事。 這樣很好。 卡艾勒姆發自內心地笑了出來,往前邁出了腳步。 |
[1] [2]
[備忘 自言備忘 匿名備忘/履歷] / 發言欄
情報 序章 第1日 第2日 第3日 第4日 第5日 末章 結束 / 最新



 過濾器
過濾器
生存者 (2)
犠牲者 (4)
處刑者 (4)
暴斃死 (0)
裏方 (10)
發言種類
普通發言
自言自語
悄悄話
秘密交談
死者的呢喃
裏方
放置信紙
發言分離
一併操作
發言種類關注
(0.21 CPUs)
SWBBS V2.00 Beta 8+ あず/asbnt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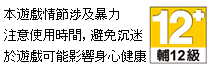
管理者:
主機:
SWBBS V2.00 Beta 8+ あず/asbnt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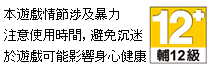
本伺服器所使用之人物圖組的著作權等均屬於該人物圖組的創作者。
請注意任何將利用人物圖組的著作素材進行複製、掃描、取樣、描線等行為
視為二次利用原創作,全面禁止該行為。
人物圖像的設計歸屬於原作者,請不要有取用造型設計當作私有原創設定的行為。
關於人物組的資訊請參閱配布元樣的頁面,所有相關使用規範皆以原頁面記載之內容為最終依據。使用的人物組相關的資訊記載於下列連結內。
深海團的獨立職業、恩惠、功能借用自人狼物語 深海國。
部分CSS風格借用自人狼物語 月狼國。
部分功能借用自人狼物語 三日月國。
【借用&參考詳細來源】管理者:
柴郡猫主機: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