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濾器
過濾器
生存者 (4)
犠牲者 (6)
處刑者 (6)
暴斃死 (0)
裏方 (10)
發言種類
普通發言
自言自語
悄悄話
秘密交談
死者的呢喃
裏方
放置信紙
發言分離
一併操作
發言種類關注
(0.18 CPUs)
SWBBS V2.00 Beta 8+ あず/asbnt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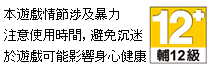
管理者:
主機:
SWBBS V2.00 Beta 8+ あず/asbnt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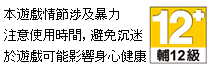
本伺服器所使用之人物圖組的著作權等均屬於該人物圖組的創作者。
請注意任何將利用人物圖組的著作素材進行複製、掃描、取樣、描線等行為
視為二次利用原創作,全面禁止該行為。
人物圖像的設計歸屬於原作者,請不要有取用造型設計當作私有原創設定的行為。
關於人物組的資訊請參閱配布元樣的頁面,所有相關使用規範皆以原頁面記載之內容為最終依據。使用的人物組相關的資訊記載於下列連結內。
深海團的獨立職業、恩惠、功能借用自人狼物語 深海國。
部分CSS風格借用自人狼物語 月狼國。
部分功能借用自人狼物語 三日月國。
【借用&參考詳細來源】管理者:
柴郡猫主機:
旭



















